【时政】沉舟侧畔
1970年代末,越南共产政权正大力迫害国内人民,其中被视为富裕的华裔首当其冲,导致一波又一波的船民投奔怒海,往东南亚各国逃亡。当时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尼都暂时收容了大量越南难民。
1979年6月,时任马来西亚副首相兼内政部长的马哈迪受外国媒体逼问,万一船民继续登陆马来半岛,政府将如何回应时,挑衅地回覆:“We will shoot them on sight”(我们一见到就会开枪扫射)。此言引起国际哗然。
 马哈迪随后在一篇文告中解释他当时的用字是“shoo”(赶走)而非“shoot”。当年外交部负责东南亚事务的主任阿末卡米尔(Ahmad Kamil Jaafar)坚持马来西亚有国际义务援助前来寻求庇护的越南人,因此成功让政府打消遣返越南难民的念头。
马哈迪随后在一篇文告中解释他当时的用字是“shoo”(赶走)而非“shoot”。当年外交部负责东南亚事务的主任阿末卡米尔(Ahmad Kamil Jaafar)坚持马来西亚有国际义务援助前来寻求庇护的越南人,因此成功让政府打消遣返越南难民的念头。
陆续遣返越南难民
直到2005年8月,最后一位越南难民自愿被遣返之时,马来西亚在将近三十年间一共收容了高达25万的越南公民,其中24万人被安置到第三国(例如瑞士、美国、澳洲、纽西兰和加拿大),剩余的一万人于1990年代开始陆续被遣返,回到政局已经稳定下来的越南。
因此,纵使马来西亚并非《1951年联合国难民公约》的签署国,毕竟还是暂时收容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周边国家的难民,肩负了一部份的人道义务。
难民公约对难民的定义是:“具有正当理由而畏惧会因为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身份或政治见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居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不能,或由于其畏惧不愿接受其本国保护的任何人。”
历史上,越南华裔并非该国原居民,这个社群在二战之后直到越战期间,还普遍被视为富裕的资产阶级。因此,当越南政府在1970年代末出于种族(原居民vs华人)和政治意识形态(共产主义vs资本主义)而迫害华裔时,后者完全符合了联合国对难民的定义。当然,吾人不该忽视与此同时,越南共产政权也在对付与其政治和宗教立场相左的其他人民。
难民、移民、移工
尽管国际条约对难民的定义如斯清楚,一般人仍然无法厘清难民与移民(migrant)和移工(migrant worker)之间的不同。尤其在东南亚,除了菲律宾、柬埔寨和东帝汶之外,其他国家都不是难民公约签署国,无论在政界、媒体和民间方面,对相关议题的讨论付诸阙如。
这当中,泰国和马来西亚因为长年引进周边国家的劳工,有证与无证(即俗称的合法与非法)皆有,形成了一个混合的移民现象(mixed migration),以致民众往往无法分辨何为难民,一律以移工待之。
 这也正是为何当数以千计因种族和宗教而受缅甸当局迫害的罗兴亚穆斯林难民(Rohingya Muslims)于数月前抵达马泰附近的水域时,引发了民间强烈的抗拒,呼吁各自的政府不让他们上岸,其中最普遍的理由即他们是“非法外劳”,浑然不知这些船民理应获得国际援助。
这也正是为何当数以千计因种族和宗教而受缅甸当局迫害的罗兴亚穆斯林难民(Rohingya Muslims)于数月前抵达马泰附近的水域时,引发了民间强烈的抗拒,呼吁各自的政府不让他们上岸,其中最普遍的理由即他们是“非法外劳”,浑然不知这些船民理应获得国际援助。
简单而言,难民是基于难民公约当中所列出的因素而逃离自身国家,到他国寻求庇护的人士,而移工(无论有证或无证)则纯粹是为了经济原因而越境进入他国。寻求庇护者(asylum-seeker),则意指难民身份尚未获得相关单位(政府或联合国难民署)确认时的个人。
一人身兼数个身份
马泰皆非难民公约签署国,因此对难民不像欧美纽澳等国家那般宽容,不允许滞留的难民或寻求庇护者工作。但难民或寻求庇护者出于生计,不得不冒着违反所处国家法律的危险,非法打工,由此衍生了一个人同时具有难民/移工或寻求庇护者/移工的情况。
回顾历史,局势动荡之时,个人往往为了生存而产生了多重身份而不知。我祖父于1920年代从中国海南岛飘洋过海南来马来亚谋生,之后再把我祖母接过来。我父亲在马来半岛出生,祖父却出于生活拮据之故,数年后将其母子二人送回海南岛。
孰知之后中日战争一发不可收拾,又托现在所谓的蛇头把祖母和父亲接回马来亚。父亲生前曾提起当时年仅七八岁的他在长达数週的行程中,不时得在破烂不堪的船只上和其他小孩抢夺发酸的饭团,南中国海波涛汹涌也意味着随时翻船,葬身大海,能够逃离战乱的中国,顺利抵达南洋,算是捡回了条命。虽然马来亚最终也难免日军蹂躏,那是后话。
史上的难民迁徙路
因此,祖母初次下南洋,是为了与身为移工的祖父团聚;当她带着孩子再次投奔南中国海时,则是为了逃离侵略者的迫害,因此拥有了难民的身份。虽然在那个年代,国际间对难民并无任何定义,遑论援助方案。
这样的例子在华人世界多的是。香港两大著名小说家金庸和倪匡,都是因为本身政治理念与中国共产党相悖而在1950年代出走到香港,成为英国殖民者治下的难民继而成为当地居民。同样的,出生在中国河南省的马华作家姚拓,1950年眼见共产势力崛起,而选择逃到香港,七年后到马来亚定居下来,身份也在之后由难民转为公民。
 其他因为文学立场与中共意识形态不符而出走,并且在南洋逗留过的中国作家还包括曾在南洋大学短暂执掌校务的林语堂,和因为华文报业路线而与李光耀发生冲突的李星可。需知文学与政治难脱干系,中共建国之初下令作家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不认同者即政治敌人,以致大量文人在1950年代纷纷逃离中国,到他方寻求庇护。放在当下的国际脉络,他们完全符合难民的条件。
其他因为文学立场与中共意识形态不符而出走,并且在南洋逗留过的中国作家还包括曾在南洋大学短暂执掌校务的林语堂,和因为华文报业路线而与李光耀发生冲突的李星可。需知文学与政治难脱干系,中共建国之初下令作家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不认同者即政治敌人,以致大量文人在1950年代纷纷逃离中国,到他方寻求庇护。放在当下的国际脉络,他们完全符合难民的条件。
难民的持续性出路
联合国难民署在甄别一个人为难民以后,下一步就是为其寻求持续性的出路(a durable solution),不外有三:自愿遣返(voluntary repatriation,例如十年前因内战结束而顺利由马来西亚回到印尼亚齐省的难民)、在地融合 (local integration,例如于1970年代中因内战而由菲律宾南部逃到马来西亚沙巴州的穆斯林难民,第一代的大约六万人最终成为马来西亚公民),以及安置到第三国(resettlement to a third country)。
只要难民的原居国一日局势不稳定,难民则一日不能被遣返。安置方面,正所谓僧多粥少,愿意接收难民的国家不多,以致全球高达六千万的难民当中,只有不到1%的人有幸被他国接收。因此,在地融合似乎成了唯一的出路。
在地融合意即难民可以成为庇护国的公民。不以民族/族群为基础的公民国家(civic nationalism),只要难民认同该国立国的原则和理念,例如相信人人生而平等、世俗民主体制、三权分立等等,要由难民成为公民并不困难,例如不少人就以难民身份成为英国、法国、德国、澳洲、美国和加拿大公民,其中越南难民就普遍被视为这些国家重要的人才和资源。
仍在建构民族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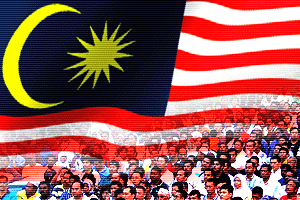 然而,东南亚国家仍然处在建设民族国家(nation-building)的阶段,对公民的定义相对狭隘,更有族群的考量。马来西亚在1970年代不让越南船民成为公民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以华裔为主,让他们在地融合可能“打翻族群平衡”(upsetting the ethnic balance)。
然而,东南亚国家仍然处在建设民族国家(nation-building)的阶段,对公民的定义相对狭隘,更有族群的考量。马来西亚在1970年代不让越南船民成为公民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以华裔为主,让他们在地融合可能“打翻族群平衡”(upsetting the ethnic balance)。
而泰国不愿意接收罗兴亚难民的顾虑则为同样是穆斯林,他们可能助长泰南马来人的分裂运动。至于新加坡,内政部于近日罗兴亚船民危机时再次重申“我们小国寡民,无力承担这方面的国际义务”。
反而印尼的亚齐省,或许感怀内战期间获得联合国难民署以及马来西亚的援助,又或许出于同是穆斯林的缘故,积极参与临时安顿罗兴亚难民的工作,虽然雅加达仍然未因此而表达任何签署难民公约的意愿,也未表示将允许难民长期居留,滞留的罗兴亚难民们的前景,依然不明朗。
其实,难民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宝贵资产。科学家爱因斯坦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都是逃离纳粹暴政的难民;知名歌手Gloria Estefan则和家人从当年动乱的古巴逃亡到美国。全球各地,不少蓬勃的社群都由难民组成,例如欧美纽澳的越南人和希腊人,以及集中在德国的库尔德族人等,为庇护国的经济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作为第一代难民/移民,他们的打拼精神往往超越原居民,也因此确保该国能够永续不断地正面发展。
简而言之,难民不是负担,而是能够丰富庇护国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群体。在东南亚的语境中,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一个自信和进步的国家,理应对弱势的难民伸出援手。毕竟人类的历史,本就是一部充满辛酸、沧桑却又往往带来完满结局的逃难和移民史。
编按:原文“关于难民的二三事”刊于新加坡双语文化志《志异》第四卷,2015年。
唐南发是联合国独立顾问,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性别少数群体,族群政治与民族主义,闲来无事喜欢研究世界各国茶文化。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